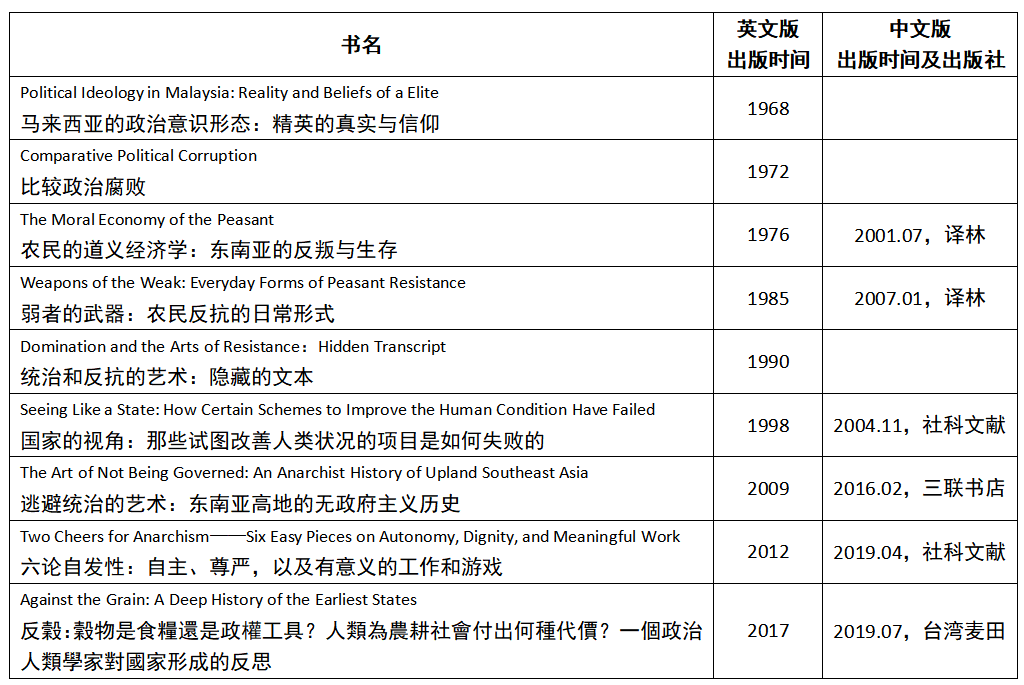从6月27日到7月2日,出了一个长差,蜻蜓点水般打卡了云南曲靖、江西新余和广东中山,加上在珠海停留的3日,总共在外面晃荡了9天。
回到成都后就复发了“差后综合症”。主要表现为身体垮塌、精神涣散、能吃贪睡、自绝于社会(不想接打回复电话微信)。虽然背负着多项不太容易的工作,但毫无生产力, 焦虑到脚趾妹儿扣紧紧。
晚上难入睡,白天随时想躺平。一感到紧张担忧,就在脑内吹口哨喊预备起,弹起在椅子上坐不了一会儿就又垮掉,而且坐着的时候还在上网冲浪,或者胡乱翻书,也没工作。一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边又吃了水果然后躺平睡着了!!!(夏日白昼真的好容易困倦)
浪费掉的时间都是要还的,我保证明天一定打起精神好好工作,灌入速溶咖啡撑起自己。立了这个旗子之后感觉好棒呀,似乎手指生风扫过键盘,写好的报告、做好的方案和PPT就在电脑屏幕上手牵手跳起舞来。
外卖叫了两斤小龙虾,算鼓舞军心吧,等下到了就充满仪式感地吃掉,为明天高效生产做好准备,嘻嘻。
这两天在看《野猪渡河》。后浪这几年持续在出台、港、南洋作家的作品(“华语文学”系列,目前19册),今年一月出版了黄锦树的《乌暗暝》(买了还没看),这个月张贵兴的《猴杯》也上架了。《野猪渡河》是去年在孔网常去的店铺闲逛时买的,一直放着没读。
仅仅翻前几页,就被密不透风的文字憋到窒息。张贵兴用词凶狠奇谲,不留余地,但是他浓稠的语言风格与南洋热带小村的人景物事特别匹配。
“痰状的雾霾散乱野地”
“夕阳被热气和烟霾切割”
“西南风使烟霭不时网住了庄稼和数百栋高脚屋”
“夕阳烧酥了”
我对东南亚特别感兴趣。第一次与这个地区发生连接是在初中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,小镇刚有了第一个网吧,上网要五块钱一小时,我攒了好些天才拿到入场券。在那个网吧我第一次使用了联通世界的聊天工具——ICQ,并随机添加了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聊天。他在马来亚大学读书,而我根本分不清马来亚和马来西亚的区别,所以一直说你们马来亚怎样怎样,直到他纠正我他的国家叫马来西亚。多年后我才通过阅读,理解那位大学生不只是在纠正我的文字,而是在纠正我的政治错误。“马来亚”是一个历史国名,也与作为族群的“马来人”紧密相关。1963年它与新加坡、砂拉越和沙巴组成联邦国家,国名也变成了“马来西亚”。那位网友当然很在意这一字之差。
我前面交替使用“南洋”和“东南亚”两个词。其实这两个概念都是被这片土地之外的人发明出来的。
“南洋”显而易见是中国人创造的,“南”在方位上与汉人住居的北方对应,“洋”则与腹地内陆对应(南洋不包括内陆可达的缅甸和老挝)。这个名词是由“我”出发识别和定位“他者”而来的。
“东南亚”最早出现在二战时期,“稳定而普遍地使用‘东南亚’一词最初是从美国开始的,就像之前的日本一样,美国企图支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整个地区。”(《椰壳碗外的人生》P44)。很显然,它是以东亚和南亚这两个坐标来定位的。
按照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的说法,东南亚这一概念“暗示了一种专属集体性,但事实是集体性难寻”。与在道德秩序、宗教观念和文学流派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东亚三国,以及在宗教、经济和传统文学方面长期有关联的南亚四国不同,东南亚国家数量多、宗教多、殖民宗主国多、语言多,内部有着巨大的异质性。那么多不同的族群交织在一起,他们彼此学习、依赖、敌视、战争、联合……也许这也是东南亚令人着迷的一个原因。
我仅仅短暂到访过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和柬埔寨。本来今年春节准备去泰国,却因为疫情没有成行。哪怕是浮光掠影地走过,也收获了无数新知和回忆。然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和海洋了。阅读东南亚的文学作品,或许是当下能做的不错选择了吧。